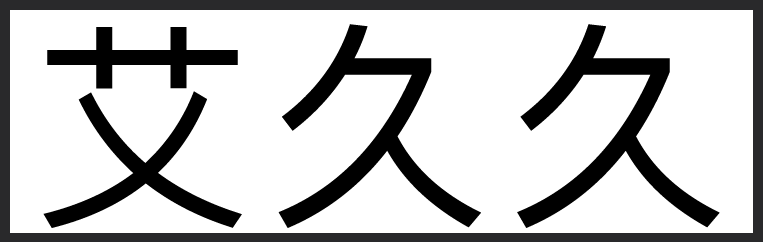唱彻黄金缕——海棠与蝶儿篇玫瑰著长篇小说...
- 爱濂说
- 2025-02-03 08:31:30
唱彻黄金缕——海棠与蝶儿篇
玫瑰著长篇小说《花落长安》番外(二)
“爷爷!”
“爹爹!”
“官老爷,爷爷不是坏人!”
“求求你们啦,不要带爹爹走!”
“锵琅琅”,一阵锁链声响,两个被布套套住的人在几名黑衣衙役的推搡下走出巷子口,一双少年男女随在他们身后哭喊,那名小女孩儿才止六、七岁光景,早哭得满脸眼泪纵横、声嘶力竭。
当先的一名红衣小吏,边驱赶巷口围观的众人,边叫道:
“海世兴、海光宗父子独得石盐经营之权而不体天恩,贪婪成性,私行囤积,哄抬市价,经人举报,查证属实,即刻拘押待审,还万民公道。乡亲们且散了罢!”
言罢分开人群率着一众衙役及海家父子绝尘而去。
那一双少年男女奋力追出一程,但终究年幼,越追离得越远,只能眼巴巴看着爷爷、爹爹被人押着消失不见。又哀哀哭了半晌,稍大些的男孩儿才扶着妹妹回转自家院子。
“海家大爷离家多年,据说前往西北京城发展了,留下海二爷独自支撑祖业。海二爷为人素来厚道,平日乐善好施,待邻里至为和气…那个官刚说什么,‘私行囤积’、‘哄抬市价’,这种事从何说起?”
“张兄,‘官¥字两¥张口,上下都是理’哇,他这‘理’,你信吗?一朝¥天¥子一¥朝¥臣,上边的人换了,就要重新定星分利。海家错了没?公平良善,你没错。但这个利你占得太久,挡了别人家的财路,该腾腾地方了,所以你也错啦。唉,我就是担心,这个海二爷是个倔死牛的…海家怕是倒喽。”
围观的百姓们纷纷议论着渐渐散去。
~~~~~~
“小阿哥你看,他们在做甚么?”
那个年龄稍长的男孩——海大公子海棠一脚门里一脚门外,忽听妹妹提醒,连忙抬头,正瞧见一瘦一胖两个身影各携着个鼓囊囊的包袱奔向后宅,定睛一看却是家中仆人五尺、负一。
海棠日常于街市间玩耍,最喜听平书、话本,见此情景,略怔一怔便即恍然,不由怒气上涌,咬牙斥一声“两个贼仆”,拔脚就追。那负一年轻,腿脚麻利,见势不妙早从后门一溜烟儿逃得没影了。海棠便直追五尺。
“负一,你这卑鄙小贼,主人待你不薄,你居然趁主人蒙难,落井下石……” 那满头白发的老仆五尺忽然放声高呼,随即转过身来,放下包袱,带着哭腔向海棠说道,“才见负一那小贼把许多财物卷作两个包袱要走,老奴虽竭力阻拦,只抢下来这个,却还是让他逃掉了……小郎君,老奴真是没用!”
海棠一怔,眼见五尺须眉如霜,上面又是眼泪又是汗水,两条腿还在不住抖动,显然是真的拼了全力了,满心的愤怒早化了一腔油然感动:
“五伯…五伯无须自责,我和宁儿如今都不知该如何做了,五伯这般忠义,实是我海家之幸。”
那小女孩宁儿也走上来轻拍五尺的手表示安慰。
“小郎君,老奴听人说牢¥里头犯¥人都不给顿饱饭吃的,对犯人非打即骂的事更是屡见不鲜,小郎君该当取些银两上下打¥点一番,也免得主人要牢¥里白吃苦头。”五尺终于喘匀了气息,向海棠建议。
“只好如此了,只是还要烦劳五伯辛苦。”
~~~~~~
三天后,新任钱塘县令升堂问案,其中就有海家父子囤盐抬价一案。那县令读罢了师爷递上来的诉状,又提了海家父子询问,不禁皱了皱眉,觉得海家父子不像是诉状上所描绘的奸险之徒,莫非另有隐情?便拿眼去问旁边的师爷。
那师爷见县令看自己,忙走上前,俯向县令耳边低声道:
“大人,您看这投诉状之人,其族叔在本州刺史府中管事。”
“如何判妥当?”
师爷扬右手在喉头虚虚一抹。
县令皱眉,觉得有些过分,又畏惧投诉人背后的势力,沉吟半晌,判道:
“今查,钱塘县商户海世兴、海光宗怀贪而囤¥积,违圣¥恩、藐法度,论罪罚¥没家产、充¥军,念其子少女幼,允留拾一。海世兴、海光宗配黔南充¥军……”
当晚,海棠、海宁得了老仆五尺带回的消息登时相拥哭成一团,好不容易止住眼泪,海棠兴觉得渺渺茫茫、无着无落,看着妹妹不由又掉下泪来。五尺建议:“小郎君的大伯与主人一般正直忠诚的,因见时世更迭,盐政跟着变来变去,担心石盐生意不能持久,遂离乡远赴京城发展。郎君何不投奔大伯去,他定然不会袖手不管?”
海棠连忙向五尺致谢。
~~~~~~
主仆三人匆匆收拾一番,第二天过午方含泪辞家赶上京城长安方向的大路。
宁儿幼小走不快,几个人不时停下来歇脚,就这样,眼看日薄西山,却走到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所在,又走了一阵,才寻了处破庙暂时歇下。
胡乱吃了些干粮,海棠哄了宁儿先睡去,自己却枕了胳膊望着天空的星斗出神:
“爷爷爹爹流徙黔南充军,从此隔山隔水,也不知是否重逢有日;京都长安,据说是天下最最繁华富庶之地,心中亦有向往,可漫漫数千里,宁儿妹妹不知要吃多少苦;幸亏五尺伯忠义,待到了长安,定得好好谢他……”想着想着,海棠恍惚睡去。
睡至半夜,蓦地一阵冷风将海棠吹醒,扭头时却不见了老仆五尺,连自己身侧装着干粮、盘缠的包袱也不见了。
海棠急跃起身跑到庙外张望,朦胧的月光下,遥遥望见五尺背着一个包袱闪进远处的树丛。
海棠又急又怒,急步追过去,哪知追了半夜,不但没追到五尺,连自己来时的路径也迷了。寻了半晌,仍只是在林子里打转。想到宁儿一个人在那破庙里,会不会害怕,会不会遇到野兽,会不会遇到坏人,不禁心中又忧又急又累又怕,再也忍耐不住,蹲在地上放声大哭。
哭了半晌,海棠抬起头,但见远处青(○)山横黛,眼前碧波潋滟,自己不知到了一处风景绝佳的所在。
沿着湖边缓缓走了一会,行上一座小桥。走到桥心,但见阳光虽明,那湖水却幽暗深邃,海棠心里蓦然萌出一股难以遏制的死意:
“不如投到这水里去了罢…
“可是,宁儿呢,没有了我宁儿可怎么活…”
心中天人交战,海棠已堪堪走到桥边。“啪”地一声,后背忽然被甚么人拍了一记。
“嗨!小阿哥,你是要捉蜻蜓吗?”一个碧玉般脆、冰糖一样甜的声音自海棠身后响起。
海棠顿时清醒,回头一看,却是个精神神、俏生生的小女娃笑盈盈地站在身后。小女娃看上去比宁儿大不了许多,弯眉笑眼,小手掩着口,脸上满是狡黠、促狭。
“噢,不…是!我正想捉一只大蜻蜓,被你一下吓跑了。
“你…你家大人呢,可不要一个人乱跑啊,万一遇到了坏人…”
“小阿哥是坏人吗?”小女娃盈盈绕着海棠转了个圈,“小阿哥是不是哭鼻了啦?好羞哦!”
小女娃的小手蓦然放下来,海棠才看清楚,小女娃小小的嘴巴大大的眼,显然是个美人(○)胚(○)子,只是这个年纪脸上带着些许婴儿肥,她抬掩口居然是为了这个缘故。
“别看我!”小女娃恍然发现海棠看她脸上,忙抬手又掩住口。
“我才不是不懂事的小孩子呢,还甚么‘乱跑’!小阿哥可是遇到了难处?求我娘,我娘可是有本事呢。” 小女娃一手掩口,另一只手轻轻朝身后指了指。
海棠顺着小女娃手指的方向望去,但向不远处莲叶田田,菡萏拳拳,却是湖水中的一片野生荷塘,塘边梨树下正泊了一艘画舫。梨花影里绰约立着一个白衣女子,云髻轻眉、朱唇一点,看上去既觉温婉,又有十分的冷艳。
海棠未语,那女子已经向这边招手。小女娃一拉海棠衣袖:“我娘叫我们呢。”
海棠有些窘,却不好意思推开她的手,只好任由她扯着走到女子面前。
还没等海棠开口,小女娃就抢先道:“阿娘,这位小阿哥刚刚要投湖,定是遇了天大的难处,娘帮他一帮吧!”海棠的小白脸登时一黑。
“不要乱说!”女子蹙眉瞪了小女娃一眼,又转向海棠,“遇见了便是缘,不知小郎君有甚么难处,不妨说一说,我们帮得上忙也不一定。”
于是,海棠把欲去京城寻大伯,途中遭家仆拐(○)了盘缠、干粮,以及自己追出来迷路丢了妹妹的事说给女子听。
女子听罢微笑:“应该无妨,这座西泠桥附近虽林子密集,却向是无野兽出没的。小郎君在此稍待,我着人去寻你妹妹来。”
~~~~~~
两个侍女去寻宁儿了,女子冷清地站在那里遥望远山湖水。小女娃儿却坐不住,一定拉了海棠要他陪自己玩耍。女子也不制止。
时间不长,桥那边远远的林子边转出两高一矮三个身影,是刚才的两个侍女寻了宁儿回来了。
女子转身面对海棠:“小郎君,你的妹妹已经寻着了,这些银钱、糕点,你拿了去罢,可解燃眉之急。”
说罢便唤了小女娃儿登船,船桨摇动,“夷犹“作响,画舫缓缓离岸。
海棠急追向岸边:“阿…阿姨,承蒙阿姨援手,不知可否赐告姓名,我们兄妹好在日后报答?”
白衣女子未动。小女娃立在舫上,绿衣飘飘,直欲凌空,忽然转首向海棠脆笑道:“我们是‘二先生’家的……师者父母心,小阿哥不用谢啦!”
海棠深深施礼,再起身时,画舫早已不见了踪影,但闻远远的歌声传来:
“妾本钱塘江上住。花落花开,不管流年度。燕子衔将春色去,纱窗几阵黄梅雨。
斜插犀梳云半吐,檀板轻敲,唱彻黄金缕。望断行云无觅处,梦回明月生南浦。”①
歌声宛转、缥缈,在绿水青山之间轻轻回荡。忽然浪起风生,一树梨花胜雪,落英缤纷。
~~~~~~
“小阿哥,这就是你和蝶儿姐姐“唯一的”一次相遇啊?
你不是跟紫衣姐姐说你只看过蝶儿姐姐一眼,不是说你们没有说过话吗…”
“呃…那么多年了,阿兄也许记错了,记错了。呵呵呵…”
~~~~~~
海棠坞后宅,二更,坞主换好了睡衣,翘首等惜薇娘子一起休息,却见惜薇拎了一只鸡毛掸子缓缓行来……笑得那叫一个春花烂漫,走得那叫一个或国央民…
“说吧,为什么说蝶儿长得像紫衣姐姐…”




特别说明:
①宋司马槱作《黄金缕》,未依历史,读者勿以为怪。
②文中称谓以便利为重,未依历史。 长春·东北师范大学
长春·东北师范大学
玫瑰著长篇小说《花落长安》番外(二)
“爷爷!”
“爹爹!”
“官老爷,爷爷不是坏人!”
“求求你们啦,不要带爹爹走!”
“锵琅琅”,一阵锁链声响,两个被布套套住的人在几名黑衣衙役的推搡下走出巷子口,一双少年男女随在他们身后哭喊,那名小女孩儿才止六、七岁光景,早哭得满脸眼泪纵横、声嘶力竭。
当先的一名红衣小吏,边驱赶巷口围观的众人,边叫道:
“海世兴、海光宗父子独得石盐经营之权而不体天恩,贪婪成性,私行囤积,哄抬市价,经人举报,查证属实,即刻拘押待审,还万民公道。乡亲们且散了罢!”
言罢分开人群率着一众衙役及海家父子绝尘而去。
那一双少年男女奋力追出一程,但终究年幼,越追离得越远,只能眼巴巴看着爷爷、爹爹被人押着消失不见。又哀哀哭了半晌,稍大些的男孩儿才扶着妹妹回转自家院子。
“海家大爷离家多年,据说前往西北京城发展了,留下海二爷独自支撑祖业。海二爷为人素来厚道,平日乐善好施,待邻里至为和气…那个官刚说什么,‘私行囤积’、‘哄抬市价’,这种事从何说起?”
“张兄,‘官¥字两¥张口,上下都是理’哇,他这‘理’,你信吗?一朝¥天¥子一¥朝¥臣,上边的人换了,就要重新定星分利。海家错了没?公平良善,你没错。但这个利你占得太久,挡了别人家的财路,该腾腾地方了,所以你也错啦。唉,我就是担心,这个海二爷是个倔死牛的…海家怕是倒喽。”
围观的百姓们纷纷议论着渐渐散去。
~~~~~~
“小阿哥你看,他们在做甚么?”
那个年龄稍长的男孩——海大公子海棠一脚门里一脚门外,忽听妹妹提醒,连忙抬头,正瞧见一瘦一胖两个身影各携着个鼓囊囊的包袱奔向后宅,定睛一看却是家中仆人五尺、负一。
海棠日常于街市间玩耍,最喜听平书、话本,见此情景,略怔一怔便即恍然,不由怒气上涌,咬牙斥一声“两个贼仆”,拔脚就追。那负一年轻,腿脚麻利,见势不妙早从后门一溜烟儿逃得没影了。海棠便直追五尺。
“负一,你这卑鄙小贼,主人待你不薄,你居然趁主人蒙难,落井下石……” 那满头白发的老仆五尺忽然放声高呼,随即转过身来,放下包袱,带着哭腔向海棠说道,“才见负一那小贼把许多财物卷作两个包袱要走,老奴虽竭力阻拦,只抢下来这个,却还是让他逃掉了……小郎君,老奴真是没用!”
海棠一怔,眼见五尺须眉如霜,上面又是眼泪又是汗水,两条腿还在不住抖动,显然是真的拼了全力了,满心的愤怒早化了一腔油然感动:
“五伯…五伯无须自责,我和宁儿如今都不知该如何做了,五伯这般忠义,实是我海家之幸。”
那小女孩宁儿也走上来轻拍五尺的手表示安慰。
“小郎君,老奴听人说牢¥里头犯¥人都不给顿饱饭吃的,对犯人非打即骂的事更是屡见不鲜,小郎君该当取些银两上下打¥点一番,也免得主人要牢¥里白吃苦头。”五尺终于喘匀了气息,向海棠建议。
“只好如此了,只是还要烦劳五伯辛苦。”
~~~~~~
三天后,新任钱塘县令升堂问案,其中就有海家父子囤盐抬价一案。那县令读罢了师爷递上来的诉状,又提了海家父子询问,不禁皱了皱眉,觉得海家父子不像是诉状上所描绘的奸险之徒,莫非另有隐情?便拿眼去问旁边的师爷。
那师爷见县令看自己,忙走上前,俯向县令耳边低声道:
“大人,您看这投诉状之人,其族叔在本州刺史府中管事。”
“如何判妥当?”
师爷扬右手在喉头虚虚一抹。
县令皱眉,觉得有些过分,又畏惧投诉人背后的势力,沉吟半晌,判道:
“今查,钱塘县商户海世兴、海光宗怀贪而囤¥积,违圣¥恩、藐法度,论罪罚¥没家产、充¥军,念其子少女幼,允留拾一。海世兴、海光宗配黔南充¥军……”
当晚,海棠、海宁得了老仆五尺带回的消息登时相拥哭成一团,好不容易止住眼泪,海棠兴觉得渺渺茫茫、无着无落,看着妹妹不由又掉下泪来。五尺建议:“小郎君的大伯与主人一般正直忠诚的,因见时世更迭,盐政跟着变来变去,担心石盐生意不能持久,遂离乡远赴京城发展。郎君何不投奔大伯去,他定然不会袖手不管?”
海棠连忙向五尺致谢。
~~~~~~
主仆三人匆匆收拾一番,第二天过午方含泪辞家赶上京城长安方向的大路。
宁儿幼小走不快,几个人不时停下来歇脚,就这样,眼看日薄西山,却走到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所在,又走了一阵,才寻了处破庙暂时歇下。
胡乱吃了些干粮,海棠哄了宁儿先睡去,自己却枕了胳膊望着天空的星斗出神:
“爷爷爹爹流徙黔南充军,从此隔山隔水,也不知是否重逢有日;京都长安,据说是天下最最繁华富庶之地,心中亦有向往,可漫漫数千里,宁儿妹妹不知要吃多少苦;幸亏五尺伯忠义,待到了长安,定得好好谢他……”想着想着,海棠恍惚睡去。
睡至半夜,蓦地一阵冷风将海棠吹醒,扭头时却不见了老仆五尺,连自己身侧装着干粮、盘缠的包袱也不见了。
海棠急跃起身跑到庙外张望,朦胧的月光下,遥遥望见五尺背着一个包袱闪进远处的树丛。
海棠又急又怒,急步追过去,哪知追了半夜,不但没追到五尺,连自己来时的路径也迷了。寻了半晌,仍只是在林子里打转。想到宁儿一个人在那破庙里,会不会害怕,会不会遇到野兽,会不会遇到坏人,不禁心中又忧又急又累又怕,再也忍耐不住,蹲在地上放声大哭。
哭了半晌,海棠抬起头,但见远处青(○)山横黛,眼前碧波潋滟,自己不知到了一处风景绝佳的所在。
沿着湖边缓缓走了一会,行上一座小桥。走到桥心,但见阳光虽明,那湖水却幽暗深邃,海棠心里蓦然萌出一股难以遏制的死意:
“不如投到这水里去了罢…
“可是,宁儿呢,没有了我宁儿可怎么活…”
心中天人交战,海棠已堪堪走到桥边。“啪”地一声,后背忽然被甚么人拍了一记。
“嗨!小阿哥,你是要捉蜻蜓吗?”一个碧玉般脆、冰糖一样甜的声音自海棠身后响起。
海棠顿时清醒,回头一看,却是个精神神、俏生生的小女娃笑盈盈地站在身后。小女娃看上去比宁儿大不了许多,弯眉笑眼,小手掩着口,脸上满是狡黠、促狭。
“噢,不…是!我正想捉一只大蜻蜓,被你一下吓跑了。
“你…你家大人呢,可不要一个人乱跑啊,万一遇到了坏人…”
“小阿哥是坏人吗?”小女娃盈盈绕着海棠转了个圈,“小阿哥是不是哭鼻了啦?好羞哦!”
小女娃的小手蓦然放下来,海棠才看清楚,小女娃小小的嘴巴大大的眼,显然是个美人(○)胚(○)子,只是这个年纪脸上带着些许婴儿肥,她抬掩口居然是为了这个缘故。
“别看我!”小女娃恍然发现海棠看她脸上,忙抬手又掩住口。
“我才不是不懂事的小孩子呢,还甚么‘乱跑’!小阿哥可是遇到了难处?求我娘,我娘可是有本事呢。” 小女娃一手掩口,另一只手轻轻朝身后指了指。
海棠顺着小女娃手指的方向望去,但向不远处莲叶田田,菡萏拳拳,却是湖水中的一片野生荷塘,塘边梨树下正泊了一艘画舫。梨花影里绰约立着一个白衣女子,云髻轻眉、朱唇一点,看上去既觉温婉,又有十分的冷艳。
海棠未语,那女子已经向这边招手。小女娃一拉海棠衣袖:“我娘叫我们呢。”
海棠有些窘,却不好意思推开她的手,只好任由她扯着走到女子面前。
还没等海棠开口,小女娃就抢先道:“阿娘,这位小阿哥刚刚要投湖,定是遇了天大的难处,娘帮他一帮吧!”海棠的小白脸登时一黑。
“不要乱说!”女子蹙眉瞪了小女娃一眼,又转向海棠,“遇见了便是缘,不知小郎君有甚么难处,不妨说一说,我们帮得上忙也不一定。”
于是,海棠把欲去京城寻大伯,途中遭家仆拐(○)了盘缠、干粮,以及自己追出来迷路丢了妹妹的事说给女子听。
女子听罢微笑:“应该无妨,这座西泠桥附近虽林子密集,却向是无野兽出没的。小郎君在此稍待,我着人去寻你妹妹来。”
~~~~~~
两个侍女去寻宁儿了,女子冷清地站在那里遥望远山湖水。小女娃儿却坐不住,一定拉了海棠要他陪自己玩耍。女子也不制止。
时间不长,桥那边远远的林子边转出两高一矮三个身影,是刚才的两个侍女寻了宁儿回来了。
女子转身面对海棠:“小郎君,你的妹妹已经寻着了,这些银钱、糕点,你拿了去罢,可解燃眉之急。”
说罢便唤了小女娃儿登船,船桨摇动,“夷犹“作响,画舫缓缓离岸。
海棠急追向岸边:“阿…阿姨,承蒙阿姨援手,不知可否赐告姓名,我们兄妹好在日后报答?”
白衣女子未动。小女娃立在舫上,绿衣飘飘,直欲凌空,忽然转首向海棠脆笑道:“我们是‘二先生’家的……师者父母心,小阿哥不用谢啦!”
海棠深深施礼,再起身时,画舫早已不见了踪影,但闻远远的歌声传来:
“妾本钱塘江上住。花落花开,不管流年度。燕子衔将春色去,纱窗几阵黄梅雨。
斜插犀梳云半吐,檀板轻敲,唱彻黄金缕。望断行云无觅处,梦回明月生南浦。”①
歌声宛转、缥缈,在绿水青山之间轻轻回荡。忽然浪起风生,一树梨花胜雪,落英缤纷。
~~~~~~
“小阿哥,这就是你和蝶儿姐姐“唯一的”一次相遇啊?
你不是跟紫衣姐姐说你只看过蝶儿姐姐一眼,不是说你们没有说过话吗…”
“呃…那么多年了,阿兄也许记错了,记错了。呵呵呵…”
~~~~~~
海棠坞后宅,二更,坞主换好了睡衣,翘首等惜薇娘子一起休息,却见惜薇拎了一只鸡毛掸子缓缓行来……笑得那叫一个春花烂漫,走得那叫一个或国央民…
“说吧,为什么说蝶儿长得像紫衣姐姐…”
特别说明:
①宋司马槱作《黄金缕》,未依历史,读者勿以为怪。
②文中称谓以便利为重,未依历史。
 长春·东北师范大学
长春·东北师范大学